袁隆平们,让中国不再遭受这样的灾难
导读:
5月22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逝世。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一直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如果无法提高,人们将不得不向自然过度索取,并寻求其他替代,结果意想不到地酿成一场旷日持久、危害巨大的生态灾难。
现在我们能够推进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修复工作,确保中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仰赖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
粮食问题关系到的,不只是民众的口腹、政权的兴衰,还有民族的长久存续。
袁隆平说:“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背后的深意正在于此。他与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贡献,也理当从这样的高度去铭记。
【文/ 查尔斯·曼恩】
中国长久以来都是人口大国,却始终只有相对较少的土地能种植庄稼、养活人民。
实际上,中国必须在水土充沛、适宜种水稻和小麦的地区收获巨大数量的粮食,这占到全国口粮总量的一半甚至更多。不幸的是,这些地区相对面积较小。
长江、黄河流域的平原都是为全中国生产粮食的关键所在,可是,都容易遭受洪灾。每个朝代都深知这个问题,以及通过治理长江、黄河来保护中国农业生产基地的必要性。
水的管理如此重要,因而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欧洲的博学之士都认为,水利是中国最重要的制度。
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将中国和有类似治水需求的地区形容为“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ies)。在他看来,欧洲避免了专制制度是因为农民没有灌溉的需求。欧洲农民自谋生计,这催生了个人主义、创业精神和技术进步的传统,这些都是中国从未有过的。
近些年来,魏特夫的论点已经不被看好了。今天大多数汉学家认为,水利主导的亚洲与非水利主导的欧洲等其他地方都一样,是多元的、个人主义化的,并以市场为导向的。
但这个形象依然很有影响力,至少在西方,中国仍过于频繁地被视为一块无差别的工人群体,像蚂蚁一样遵照国家指令来行动。然而,对前辈思想家的挑战并不会动摇一件事:中国有利于水稻和小麦种植的土地相对来说太缺乏了。
哥伦布大交换
从这个角度来看,哥伦布大交换是很大的恩惠,中国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它。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中写道:“在旧世界,没有哪个大规模的人类群体比中国人更快地接纳了美洲的粮食作物。”
甘薯、玉蜀黍、大花生、烟草、辣椒、菠萝、腰果、树薯(木薯),所有这些都流入了福建(通过大帆船贸易)、广东(通过澳门的葡萄牙船)和朝鲜王国(通过日本人,他们是从荷兰人手中获得的)。这一切都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谁能想象,若没有成堆的辣椒,今天的川菜会是什么样子?
“跟随科尔特斯攻陷特诺奇蒂特兰的男人们还健在的时候,”克罗斯比说,“大花生就已经开始在上海附近的沙质土壤中长大了;玉蜀黍将中国南方的田野变成了绿色;甘薯即将成为福建穷人的主食。”
甘薯的到来对福建来说是件幸事。它在福建省的传播赶上了明王朝的灭亡,以及由此引发的连年暴乱。
为了切断明军残部/倭寇的补给,清军强迫从广东到山东——纵贯中国东部整条“突出部”的沿海居民,全部往内陆迁徙。从1652年开始,士兵们列队进入沿海村庄、烧屋推墙、捣毁祠堂;往往只提前几天给出警示,就让成千上万户人家只带着衣物撤离。所有私船都被焚毁或凿沉。掉队的人都会被杀。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从海岸线往内陆延伸远至约80千米的地方都成了无人区。这是一种焦土政策,只不过烧焦的不是敌人的土地,而是自己的。
对福建来说,从沿海迁离显然是比明朝禁止出海贸易更苛刻的政策。在17世纪30年代,政治动乱和贸易禁令出现之前,每年有20艘或更多大舢板开往马尼拉,每船都载有数百个商贩。随着迁徙政策的实施,出海船数降至两三艘,并且都是非法的。
清政府让沿海居民内迁,也给朝廷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正如江苏布政使慕天颜所抱怨,关闭白银贸易实际上冻结了货币供应。由于白银一直被消耗、湮没和窖藏,中国的货币总量其实在萎缩。
清政府不情不愿地批准了他的请求,在1681年解除了海禁。然而与此同时,沿海居民正如潮水般涌入福建、广东和浙江的山区。不巧的是,这些地区已经有人居住了。
大部分居民都属于一个特殊族群——以其土楼而闻名的客家人。
早在迁徙发生前几十年,福建学者谢肇淛就已观察到,山区的客家人“楼上架楼”地住进每一处可利用的屋舍:无尺寸隙地……可谓无遗地矣。
由于无法养活自己,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贫穷的客家人和其他山区居民不得不向北、向西移民,租赁邻省无人居住的高地区域,那里过于干燥且地势陡峭,因而不宜种水稻。他们砍伐、焚烧林木和植被,然后在裸露的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能用于生产靛蓝颜料的植物。
经过几年的刀耕火种,山上薄薄的土壤层被耗尽,客家人又继续迁徙。(“食尽一山则移一山”,顾炎武抱怨道。)当沿海难民涌入山区,高地地区人口的流失也在加速。无地且贫困的客家难民被讥讽地称为“棚民”,即住在窝棚里的人。
顾炎武
严格来说,棚民不是流浪者;他们租赁了那些山谷土质较肥沃地区居住的农民所拥有但不使用的土地。棚民从一个临时居所迁往下一个,最终遍布了一片长达1500英里(约2414公里)、弯曲的中国丘陵地带,从东南部省份福建的锯齿状山峦延伸到西北部黄河流域的绝壁。
无论是大米还是小麦——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两种主食,在棚民租赁的边界土地上都无法生长。土层太薄不适合种小麦;而在陡坡上种水稻,为了灌溉就需要修梯田,租赁者不太可能承担像这样成本巨大又极其艰苦的土地改良工程。
几乎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美洲作物:玉蜀黍、甘薯和烟草。玉蜀黍可在土质糟糕到令人惊讶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快速生长,其成熟时间比大麦、小麦和粟都短。
玉蜀黍由澳门的葡萄牙人引进中国,甘薯则能在连玉蜀黍都不能生长的地方种植,它能耐受土壤酸性很强、有机物极少、养分很少的条件。
甘薯甚至不需要太多阳光,一位农业技术改良者在1628年指出,“即市井湫隘,但有数尺地,仰见天日者,便可种得石许”。
在南方,很多农民餐餐都围着甘薯打转:烤甘薯、煮甘薯、用甘薯磨的粉做面条、将甘薯与腌菜一起捣烂,或裹着蜂蜜炸透,或切碎后与大头菜和豆腐一起炖,甚至还有用甘薯酿的酒。
在中国西部,遍布大地的是玉蜀黍和另一种美洲来的进口物种:土豆,最早在安第斯山脉培育的作物。
当漂泊的法国传教士谭卫道(Armand David)住在陕西一处偏远、贫瘠地区的小茅屋生活时,他的饭食安排除了几个配菜外,几乎和在印加帝国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小屋附近种植的唯一一种植物就是土豆,”他在1872年记录道,“玉米粉和土豆就是山区人民的日常食粮;它通常和植物块茎混在一起煮着吃。”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棚民住在山上。
也许是希望通过隐瞒问题来逃避解决问题,清朝官员在人口普查报告中遗漏了他们。但所有证据显示,其数量并不小。
1773年,在福建西边的邻省江西,一位恪守规则、一丝不苟的布政使坚持要将棚民——其中许多人已在江西居住了数十年——算为本省的实际居民,并将这个情况写到呈交京城的报告中。
他派人去当地清点、记录每一个客家人和每一座客家人窝棚。在山道崎岖的赣县,他们统计到了58340名常住居民,大部分集中在县城赣州,而周边的山区却有274280个棚民。
县复一县,这样的故事不断重演,有时有数千流民,其他时候有10万甚至更多。在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超过100万的棚民已经以刀耕火种的方式横穿过整个江西了。
正如清廷也一定已经意识到的,这还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省份。与棚民同时外流的还有第二波规模更大的、流动轨迹与前一波平行的移民潮,他们进入的是极其干燥、多山而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
为了寻求社会稳定,明政府曾禁止人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完全相反的是,清政府积极推动西迁运动。与19世纪美国鼓励公民搬到西部和20世纪巴西激励人民深入亚马孙流域很相似,中国的新统治者相信,填补渺无人烟的地方对国家命运是至关重要的。(“空”,那是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其实早已有许多少数民族在此居住了。)
受到税收补贴和廉价土地的吸引,来自东部的移民蜂拥进入西部山区。大部分新来者就像棚民一样,贫穷、仕途不济、遭城市精英蔑视。他们看到,眼前风化的、峭壁嶙峋的景观是如此不适合种水稻,于是他们也选择了美洲作物。
据位于四川的西南大学历史学家蓝勇研究,1795年四川还是一个空旷而广阔的地方:其面积比加州还大,但人口只有900万。在它全部的地表面积中,只有约5957平方公里——洛杉矶县面积的一半——被认为是适合耕种的。
之后20年里,美洲作物扩散到了山脊和高地,将农田总面积增至约9583平方公里。随着四川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它的人口也增加至2500万。
这个过程与陕西省发生的事情很相似,陕西是四川东北面人口更稀少的邻居。移民涌进了两省交界的陡峭、干旱的山区,他们砍倒斜坡上的林木来为甘薯、玉蜀黍以及后来的土豆腾出空间。耕地数量猛增,于是这些耕地上产出的粮食数量也上升,然后增长的就轮到了人口。
近2000年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是非常缓慢的。但这在暴虐的清朝掌权后的几十年内彻底改变了。
从新王朝建立伊始的美洲农作物传入,到18世纪末,中国人口狂飙式地增长,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增长的确切规模,许多人认为人口大致增加了一倍,达到3亿人。不论精确的数字是多少,数字上的巨大跳跃势必带来巨大影响。正是人口激增让这个国家变成了“拥挤”的代名词。
马尔萨斯式插曲
洪亮吉1746年出生在长江口附近,他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一个知名的水道研究学者,他重新确立了行政边界,并参与了清帝国综合地理志的修撰工作。
然而,他最杰出的思想成就在当时却几乎未引起注意。在1793年,洪亮吉提出了一个前人从未有过的观念。
洪亮吉被派往西南腹地的贵州省督察学政。从中国中部涌进来的移民爬上山、种玉米、组建家庭。
洪亮吉很疑惑这股热潮能持续多久。“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他写道,或许我们可以谅解他文中的夸张,“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洪亮吉承认,清政府确实开辟了新的农田来养活中国人口。但耕地量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
洪亮吉
五年后,英格兰也有一个人提出了类似观点,那就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他是英国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在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的人,也就是第一位专业的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陷阱”引发了爆炸般的反响。相比之下,洪亮吉则完全被忽视了。
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是,他从未系统地发展自己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他把全部精力都用来抨击他认为正在劫掠国家财富的腐败官员了。
洪亮吉不被认可是不应该的;他似乎比马尔萨斯更准确地捕捉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运作机制。
马尔萨斯的理论提出了一个简单预测:更多的粮食会导致出现更多吃饭的人、导致更多苦难。
然而事实上,全球农民收成的增长速度更快。1961至2007年间,全球人口大致增加了一倍,而全球小麦、水稻和玉蜀黍的收成则增长了两倍。
所以,在人口总量飙升的同时,长期营养不良人口的比例却在下降,与马尔萨斯的预言恰恰相反。当然饥饿仍然存在,但普遍来说,儿童营养不良的概率已经平稳地、令人振奋地下降了。
相比之下,洪亮吉做出了一个相关但更复杂的预测。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持续地要求增长将引发一场生态灾难,它最终将导致社会功能失调,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所遭受的严重苦难。今天的研究者在谈到“马尔萨斯陷阱”时,指的正是这个过程。
事实上,当下所有围绕环境的争论都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第一,人类能否继续积累财富和知识,就像工业革命后发生的那样;第二,这个积累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地下水的消耗、气候变化——会不会突然扼紧“马尔萨斯陷阱”的咽喉,将地球带回到前工业时代的不幸境地。
令人惊恐的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后者的可能范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美洲作物进入中国高原地区后的几十年里,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社会因为与自身环境的斗争而陷入了剧烈动荡——一场毫无胜算的败局。
“山之露石”
从清政府开始恢复白银贸易的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80年代,邻近上海的大米贸易中心——苏州的米价涨到了过去的三倍以上。但人民收入并没有跟上,这正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因素。
据经济史学家全汉升研究,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在于涌入福建的白银,它拉高中国食品价格的方式,与早前进入西班牙的白银抬高欧洲商品价格的方式一模一样。
或许人口爆炸也加大了需求,进一步推高价格。政府为国家粮仓采购的行为,有时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
但价格上涨还有一大原因,那就是许多农民已经不再种水稻了。清朝皇帝曾以改善交通网络为第一要务,以便让农民能售粮获利。政府的目的是促进粮食流通;新的道路能帮助客商将大米和小麦从粮谷丰收的地区,运到供应紧缺的地区。
但事与愿违的是,小农们发现如果从种植水稻和小麦改成种植甘蔗、花生、桑树以及最重要的烟草,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
最初,清朝廷打击这种调换行为,坚持让农民种植“养命之宝,即赖之以生”的米谷,也就是水稻和小麦。“烟叶一种,于人日用毫无裨益,”1727年,雍正皇帝在谕旨中说,“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也。”
清代烟草颇为流行
但随着朝廷日渐保守、腐化——这似乎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宿命——它对监管正当的农业生产失去了兴趣。
农民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遇。种烟草需要种水稻所需的四到六倍的肥料和两倍的人工,但利润也更大;中国日渐壮大的尼古丁成瘾者大军愿意为烟杆子而非粮袋子付更多的钱。(有些人烟瘾翻倍了:他们将鸦片掺进了烟叶。)
据广东的农业史学家陶卫宁研究,烟草几乎出现在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有些地方的烟草问题尤其突出:在陶卫宁考察的两个典型丘陵地区中,总耕地中有“近一半”用于种植烟草。因此,当地的米价以及最常见的蔬菜、水果的价格都涨了一倍。农民最终不得不用他们的烟草收益来购买从中国其他地方运来的高价粮食。
和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情况一样,种植烟草让土地肥力枯竭。当农民把一片曾作稻田的田地中的土壤消耗殆尽后,他们会移往下一片。就这样,他们用完了所有稻田,然后就进了山。
整个18世纪,中国各地将玉蜀黍和甘薯挤塞进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处缝隙,在1700年至1850年间,棚民和移民让这个国家的种植面积几乎增加了两倍。
为了开辟必需的农田,他们砍伐了许多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森林。失去林木的遮蔽,山坡再也不能蓄住雨水。土壤养分从山丘上被冲刷下来。最终,养分耗尽的土地甚至连玉蜀黍和甘薯都无法滋养了。于是农民会砍伐更多的森林,这个周期又再一次开始。
毁坏最严重的是华中地区东部陡峭、险峻的山区,也就是棚民的家园。这个地区常见的锤击般的暴雨,不断把土地中的矿物质和有机物质冲出。风化了的土壤无法蓄水——“十日不雨,”当地县志作家在1607年记录道,“土燥坼如龟文。”
从玉蜀黍和甘薯能在此生长的角度来看,这片土地是可以耕种。但若不用铁铲撒播大量石灰或其他灰烬来降低土壤酸度,若不泼粪来增加有机质含量,若不施肥来提高氮和磷的含量,就根本不可能从这片土地上每年收获两茬作物。
有人回忆,棚民是从山下河谷流域的地主处租来的农地。租期短而且固定,没有激励机制鼓励他们让土地变得肥沃,即使他们想去做也缺乏方法。
由于不熟悉这种新作物,他们会犯初学者的错误。没有像交错种在坚硬地块上的小麦和粟,玉米被分行种植,且行距很大。许多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玉米田空出了很多土地,直接暴露在雨水下。
还有一些人没有围绕山坡横向种植,而是从山顶到山下纵向种了一排排笔直的玉米,他们不懂这种做法会引导雨水直接冲下山坡、加剧水土流失。
当山地被植被覆盖时,它们释放雨水的速度是很缓慢的;洪水也很罕见。将陡坡上的林木替换为临时栽种的玉蜀黍和甘薯地块,这削弱了山体储水的能力。雨水大片冲下山丘,掀起了洪水。
洪水淹没了水稻,但之后又让稻田干涸,因为堤坝无法再为它们拦水了。由于砍伐森林,棚民不仅让自己周围的土地荒废,还成为了摧毁下游数英里范围农业基础设施的帮凶。因为这一切发生在长江下游,棚民实际上是毁坏了这个国家农业中心的一大块。
有些当地人很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1823年,当久居城市的学者梅曾亮抱着怀旧之心,拜访童年居住过的山城时,曾向老邻居打听棚民的事情。他们的回答,即使是今天的任何生态学家也不能再补充什么。
未开之山(村民告诉他),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今(棚民)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
山地高处发生水土流失,导致下游地势较低的长江河谷区的稻田被淹没,这进一步推高了大米价格,反过来又促进了高地的玉蜀黍种植,最终导致更多河谷处的稻田被淹没。
随着棚民陆续搬入山中,洪水变得越来越频繁。在宋代,帝国发生重大洪灾的频率为每两年大约3次。在明代,一些农民——其中多为客家人——非法迁入山区、砍伐林木;不难预见的是,暴发洪灾的频率增加到每年约2次。
而清代大力推动往山区、林区移民;如影随形一般,移民的激增引发了森林砍伐的泛滥;洪灾发生率增至过去的3倍之多,每年有超过6次大洪水。
更糟的是,洪水主要袭击的是中国的农业中心。翻阅了私人笔记、县志、省志和帝国的救灾纪录后,历史学家李向军统计出清朝共发生了16384起洪灾。绝大部分都规模较小。不过,其中有13537起发生在长江与黄河下游肥沃的农田区。并且洪灾还在增加。
1841年至1911年间,清朝每年需应对13场大洪灾,有一位历史学家向我形容,这相当于每月遭遇一次卡特里娜飓风。“政府在国内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要应对接连不断的灾害,”他说,“这里是养活全国人民最关键的地区。情况很糟糕。”
清末洪水
浙江省的官员因问题的不断恶化而恐慌,1802年,他们宣布政府将受鄙夷的棚民“逐回原籍”。他们还禁止在山上种玉蜀黍。但效果微乎其微。1824年,官员再次做出尝试,彻底禁止种植这个物种,浙江被划定为一个无玉米区。但效果同样微乎其微。
清帝国的中央政府有一套“监察御史”体系,他们受皇帝委托去稽查、铲除无能与贪污者。浙江的监察御史多次请求京城派兵来铲除玉蜀黍。但是没有得到回音。在这样一种令人对人类的自我治理能力感到绝望的现象中,19世纪上半叶开荒的速度实际上竟然还加快了。
浙江的御史汪元方对此不理解。他知道,过去地主们并不清楚租赁山上闲置的土地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但“今(1850年)则水之受淤如此,田之积沙如此,山之露石又如此,官民皆知大害矣,而不能禁者,何也?”
之所以“不能禁”,部分原因是大规模非法移民的内在问题。要驱逐大量人口,强迫他们离开花费许多年才建起的家园和家族,而又不制造大量苦难,这并不容易。需要民众支持的政府会尽量减少制造这种痛苦(除非在某个群体中失去的支持能通过另一个群体增加的支持来弥补)。
从逻辑上看,这些人数十年前就离开了原来的家乡,要为他们寻找安置目的地也是一大难题。在棚民的这一例子中,政府管理的混乱或令人恶心的政策都不是主要障碍。关键问题在于,水土流失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为造成的难题。
一个法律漏洞的存在,决定了租金收入与农耕收入不同,前者无须交税。因此,在高山地区有可出租产业的地主就获得了一个轻松且免税的收入来源。
随后出现的滥砍滥伐或许会毁坏他们在河谷地区的土地,但这个风险是整个区域共同承担的,而地主的利润却是属于个人的。吸纳所有的利益而只承担一小部分痛苦,当地的商业利益打压了每一次控制棚民的努力。
在环保主义者的噩梦中,短视的、追求小规模利益的行为,最终导向了长期的、大规模的灾难。持续性的洪水引发了持续性的饥荒和持续性的动荡;修复饥荒和动荡所造成的破坏又消耗了国家的资源。
来自美洲的白银或许将明王朝推向了崩溃边缘;而来自美洲的农作物则毫无疑问地破坏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基础。
当然,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一场客家裔神棍掀起的叛乱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接连数位软弱的皇帝竟默许了官僚体制在无所作为与贪污腐败中继续沉沦。
这个帝国在战争中两次败给了大不列颠,不得不割让对边界的控制权。英军肆无忌惮地传播着鸦片,而清政府曾为了抵制其传播而与不列颠开战。灾难就像成功一样有很多缘由。
然而,狂暴的欧洲军队并不知道,正是哥伦布大交换为他们的道路扫清了障碍。
后来,黄土高原开展了更多的垦荒运动。这个地区的森林大部分都被砍光了,但在最陡峭的山坡上(因太陡峭而无法耕种)还覆盖着低矮的灌木丛,它们尚能防止水土流失。而这些土地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成为了改造梯田的对象。
梯田的田壁单纯由夯实的土构成,经常坍塌;在我拜访的一个位于黄土高原上的村子里,一场雨后,近半的村民都在用铲子拍平田壁,以此来夯实正在坍塌的梯田。即使在梯田没有发生垮塌时,大雨也冲走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和有机质。
因为黄土容易被侵蚀,每场雨都会造成梯田塌损,维护成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来源:《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
走在窑洞之间陡峭的山路上,我所看见的梯田几乎像是要滑入水中一般。因为水土流失带走了营养物质,新开垦的土地的收成迅速下降。为了维持产量,农民开垦和修造了更多新梯田,这反过来又加重水土流失,这是一场关于“恶性循环”的典型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启动了停止砍伐森林的计划。北京发起了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生态项目,“三北”工程。
如今,村民开凿出来的许多梯田已经退耕还林。政府正在试图消除全球白银贸易偶然制造的遗留问题。
(本文摘编自《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中信出版社)
——————————
《科工力量》的付费专栏,最近上线了,我们将用23讲的内容,基于中国视野,全面解析全球供应链变换之路。
从中国工程机械产业逆袭、到高铁大飞机的落地、再到芯片行业的血雨腥风,一个个精彩甚至离奇的故事,见证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5个月筹备
23期课程
近400分钟时长
现在购买还有7折优惠
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听冬晓讲故事吧!
文章版权声明:除非注明,否则均为zy的个人网站原创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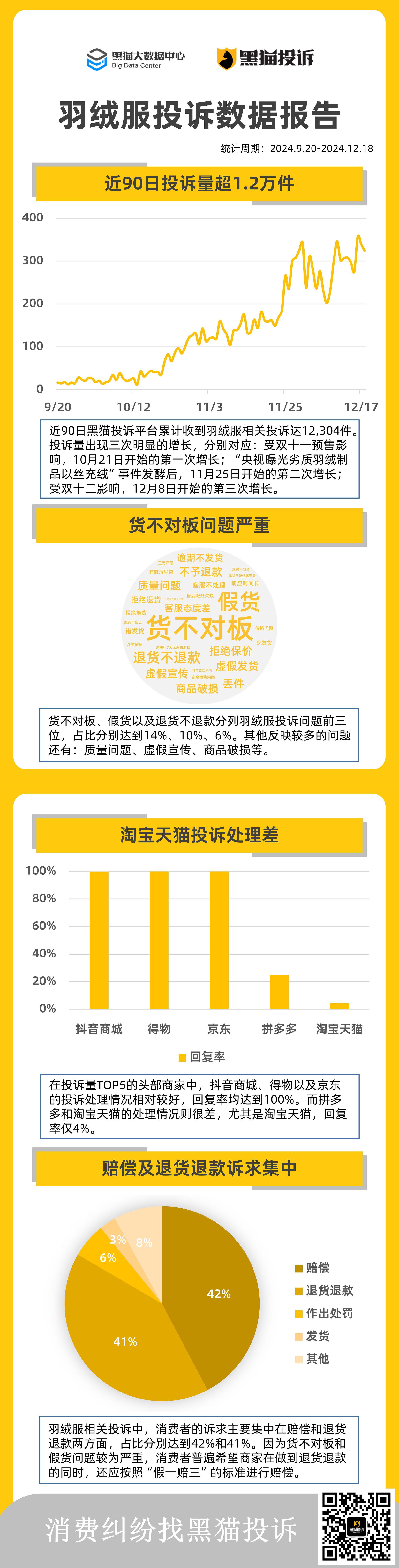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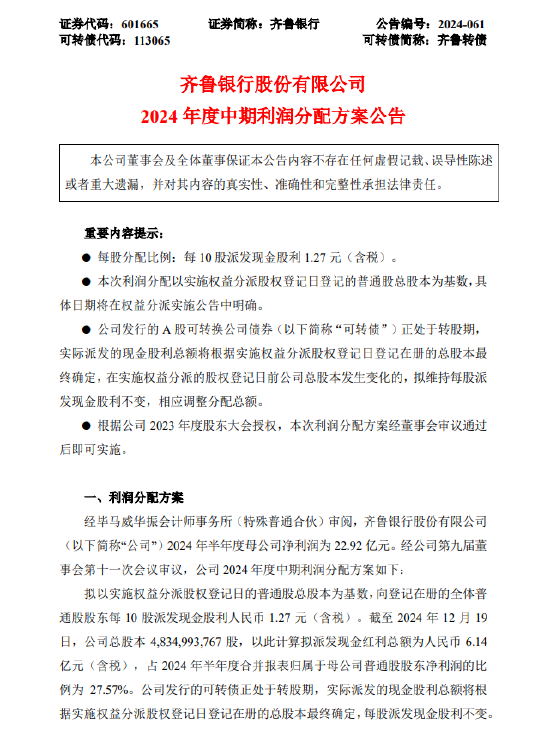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